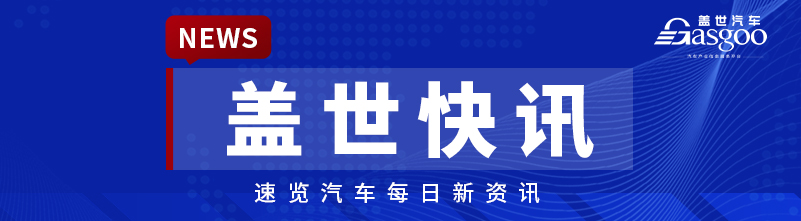专家专论 | 彭立新:汽车人才困境如何破?
从底特律的内燃机设计室到康明斯氢能源的中国布局,从跨国企业的技术高管到湖南大学的三尺讲台,彭立新教授40余年的职业生涯,恰是中国汽车产业从“内燃机依赖”向“能源多元化”转型的一个缩影。
这位见证过行业黄金时代、推动过技术跨界突破的“老汽车人”,正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人才培育的“试验田”中。在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教授、原康明斯副总裁、盖世汽车智库专家彭立新看来,当下汽车行业的核心矛盾,早已不是“缺人”的数量问题,而是“缺人才”的质量困境。

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教授、原康明斯副总裁彭立新,图片由本人提供
当内燃机时代进入倒计时,唯有重构人才培养逻辑,才能跟上新能源革命的步伐。
内燃机时代倒计时,转型势在必行
内燃机时代进入倒计时,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
“我一直在做内燃机,大学的专业就是内燃机,毕业以后的工作也全都是围绕着内燃机的,从来没离开过内燃机这三个字。”彭立新这样介绍自己。他认为,能源与动力产业和技术正在发生快速变化,在时代发生改变的时候,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,去适应时代的变化,进而成为推动改变的一份子。
彭立新的话语里,没有对传统动力的执念,只有工程师对趋势的清醒判断。他认为,产业转型从来不是“一刀切”的替换,而是新旧动力的长期共存。
当被问及“2030年内燃机是否会消失”时,彭立新并不认同“全面淘汰论”。“商用车柴油机的某些优势,现在新能源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很难超越,到2030年,甚至纯内燃机动力还会存在,传统内燃机仍会有市场,至少在商用车领域会是这样。”彭立新说。

彭立新教授教学现场,图片由本人提供,AI进行清晰度处理
不过,“有市场”不代表“能守成”。
彭立新观察到,商用车领域的能源结构已在悄然重构。过去几个月,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已达30%,虽然多集中在短途场景,但随着电池成本下降、回收技术突破,应用里程半径实现持续增加是必然趋势。另外,氢燃料电池汽车虽然已推广数千辆,但“问题不在动力本身,而在于氢”,当绿氢成本降下来、储运技术突破后,就能真正走进道路交通领域。
这种产业变革的浪潮,已经直接传导到了人才市场。特别是不少动力专业的学生,普遍焦虑“专业要被淘汰”,甚至面临就业困境。
对于此,彭立新十分坦然,“有压力是正常的,但根源不在他学的什么专业,而在于他有什么心态。”他以自己为例,40多年里做过无气缸盖、无曲轴、无冷却系统的各类新型内燃机,“我从没觉得内燃机就该是‘活塞 曲轴’的样子,它本质是‘满足市场与法规的动力装置’”。
更关键的是,在彭立新看来,内燃机专业是“跨学科的富矿”,涵盖化学、机械、电控等领域,“只要心态放开,这些基础能支撑你转去做动力电池、做氢燃料、做智能控制”。
反之,若固守“我只懂内燃机”,则必然被时代淘汰。
汽车新时代不缺人,但是缺人才
“康明斯在中国招了很多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,但毕业生的质量很难满足企业要求。”彭立新的这句话,点破了当下汽车行业的人才困境。
他在中国执掌康明斯工程团队期间,公司工程师从数百人扩张到了近2000人,但刚进来的无论是本科生、研究生还是博士生,都有着“浓烈的应试教育的痕迹”。彭立新认为,“是现在的教育耽误了孩子,大学这四年至关重要,但是如今的教育方式,使得很多人都浪费宝贵的机会。”
问题的根源,就在于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现代技术发展和产业需求的严重脱节。“我们现在的教育,还在沿用着老旧的模式,专业分得太细,教材十年不变,老师盯着论文,学生盯着考试。”彭立新对此深感忧虑。
他见过太多毕业生进了企业后,等着领导布置任务,做完了也不知道对错;抛出一个工程问题,只会找“已知条件”,不会从千个“未知因素”里筛选关键变量。“这就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后遗症,考试是‘用给予的五个已知找一个未知’,但解决工程问题需要‘从千个未知里抓出五个关键’,很显然,认知结构和能力模型完全不一样。”彭立新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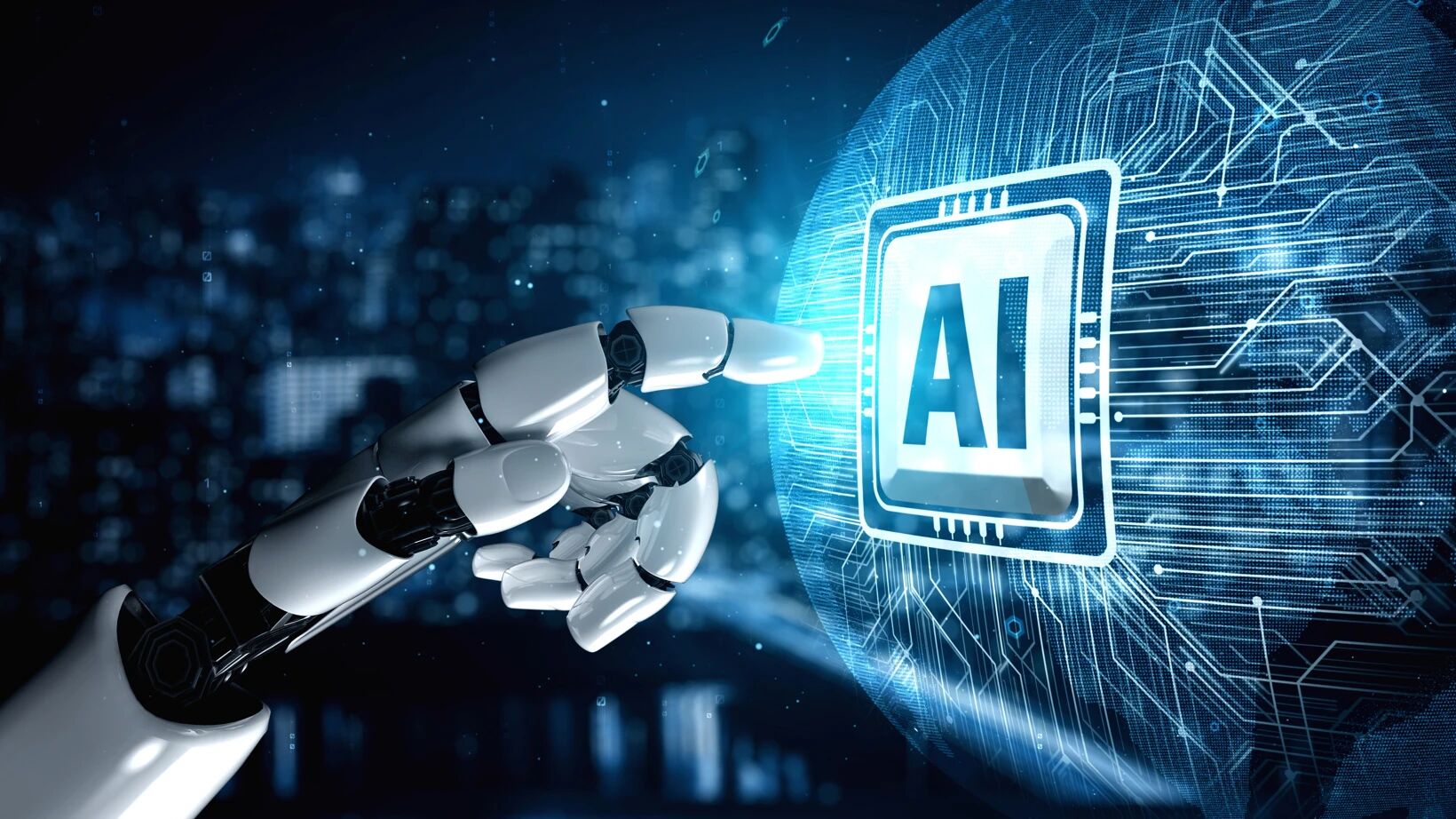
图片来源:摄图网
更矛盾的是,行业看似“内卷裁员”,实则“缺才如渴”。当下汽车行业正处于“电动化、智能化、网联化”的三重变革之中,AI正在替代重复劳动,但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、具备系统思维的人才却愈发稀缺。
“我常说,要培养‘包工头型’人才,不是‘打工仔型’。”彭立新解释,“打工仔”只会执行指令,而“包工头”能把一个复杂项目拆解成小任务,然后协调资源解决问题。“AI将在不远的将来替代各种‘打工仔’的岗位,而不是‘包工头’的位置”。
中国正在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,实现技术上从跟跑向并跑、领跑的转变,“这种变化下,企业需要的不是‘会画图、会计算’的技术员,而是有创新精神、懂市场、懂法规、能协调全球资源的合格工程师。”
但现实是,高校在传统模式下培养的“老产品”,根本跟不上产业的“新需求”。彭立新感叹到:“如果学校是工厂,生产的 ‘产品’没人要,早就该倒闭了。我们这种特殊的教育体系,还在不断批量输出着不符合市场的‘老人才’。”
更严峻的挑战来自技术迭代速度。彭立新观察到,现在汽车行业的技术周期已从“十年一代”缩短到“半年一变”,各类新技术和工程工具不断涌现,但高校学生还在花大量时间,学习那些毕业后根本用不上的传统的“内燃机燃烧理论”、“机械制图”等课程。
彭立新直言,行业不缺“能考90分”的学生,缺的是“能解决实际问题”的人才;不缺“懂单一技术”的专才,缺的是“跨领域整合”的通才。
探索新汽车时代人才培育模式
“我回湖南大学,就是想做个教育改革的试验,希望能够打破传统模式,探索一条能够培养真正适应新时代要求人才的途径。”2022年,彭立新退休后选择回到母校,在学校领导的全力支持下创办了“未来能源与动力教学创新改革实验班”。
“未来能源与动力实验班”名字颇有深意:不叫“新能源与动力实验班”,担心局限于纯电动领域,也不叫“氢能源与动力实验班”,担心未来技术方向有变化,而是“未来能源与动力实验班”,意欲跟着产业趋势走,产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,就培育什么样的人才,让学生一毕业就成为“有用之才”,这是“以学生为中心”办学宗旨的一大体现。
这个实验班从一开始就打破常规。对课程进行重构,加重基础课程,删去或“贯通”那些“被边缘化的课程”,强化“实践环节”,缩减课堂内的学分数,腾出时间让学生做项目。
采用新的培养模式,就是要塑造学生的“工程师基础”。比如,流体力学和机械设计等核心知识的学习,要通过具体项目来落地,学生要设计一个“自己的”风机叶片,用3D打印做出来,再放到风力发电试验台进行性能测试”,让学生知道,学流体力学和机械设计是为了优化叶片结构,不是为了考试。
试验班的“贯通式项目”,按新能源行业的上下游领域划分。以氢燃料电池模块为例,分成可再生能源发电、电解水制氢、氢燃料电池、动力整车四大模块。
“大一了解系统,大二做计算机仿真和机械设计,大三完成机械制造,大四把产品装到小车上试车”。彭立新解释,实验班每个学生都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工程流程,“具体做哪一个模块不重要,就像走进健身房,用哑铃还是杠铃不重要,关键是要练出‘解决问题的肌肉’。”
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,实验班不惜以“带研究生的方法带本科生”。为贯通式项目建设专用的实验台架、项目专用的工作室,为每一个学生配备来自学校和企业的导师,每一个学生都有在四年内必须完成的工程项目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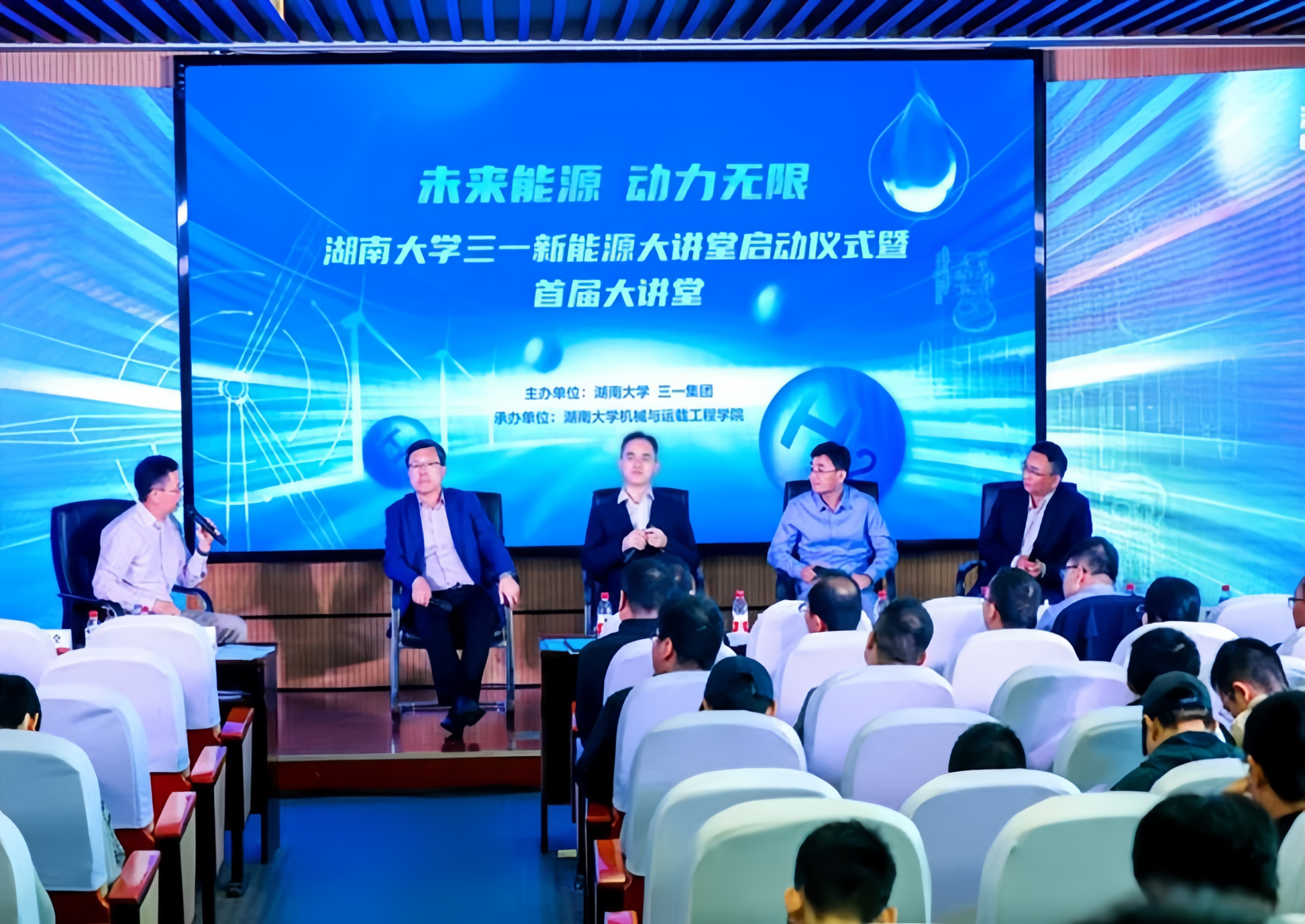
湖南大学三一新能源大讲堂现场,图片由彭立新提供,AI进行清晰度处理
另外,实验班还积极推进校企联动,让学生“提前看见真实的行业”。试验班的背后,是三一、康明斯、汽研院、玉柴、湘油泵等企业“真金白银”的支持,他们选派专家来校讲课、担任企业导师、共同编制教材,提供实物和资金支持,开放企业项目案例,开放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和全球一流的研发中心让学生游学,甚至直接提供新员工培训大楼,把3个月的企业培训压缩成2周实习,让学生获得“吃压缩饼干”式的职场体验。
实验班的成效,比彭立新预期的更快显现。湖南大学能源与动力系原来是一个“冷门专业”,2022年时的第一志愿报考率仅38%,大一年底有40%的学生想转至其它专业;现在成了“热门专业”,2024年实验班的第一志愿报考率飙升至80%,换专业时竟有60人排队想进来,“要通过严格的面试筛选,保证不开后门”。
更让他欣慰的是学生的变化。彭立新时常能听到外系老师这样的评价:“能动系的学生在课堂上更活泼,会主动参与问题的分析,不像其他系学生只是被动听讲”。在企业端,那些在背后支持的各大企业的高管来学校都纷纷提出“希望你们的毕业生全来我们这工作”。
当然,实验班的挑战也不少。比如,老师们已经习惯于靠固定教材上课和论文成果获得职称评定,而实验班要求老师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,要带项目、陪学生做试验,这些“看不见成果”的工作,短期内无法转化为评职称的依据。“学校也在根据需求逐步优化晋升政策,强化本科生教学的比重,今年我们还拿了个教学改革一等奖,激励相关老师的奉献。”彭立新介绍说。
当问到实验班的模式是否能够被“复制”时,彭立新坦言,很难完全被复制,但是可以借鉴。实验班获得的行业资源、企业的支持、学校的政策倾斜等,都很难被其他院系或者学校完全复制。就像深圳改革开放的具体做法不能直接搬到长沙,但深圳的经验长沙是完全可以学习借鉴,“比如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思想,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、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思路等,其他院系和学校都能学习与借鉴。”
对于未来,彭立新把目标锚定在2030年,这正是中国碳达峰的关键节点,也是他预判的新能源行业“拐点”。“2030年,固态电池能否商业化、绿氢能否成为新能源的成功载体等问题都可望获得答案,新的能源格局与动力变革会更加清晰。”
实验班的前面几届学生都会在2030前后毕业,正好赶上拐点。“我希望这些学生能带着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和工程能力走进行业,成为2030年汽车新时代的中流砥柱。这比我自己早年搞出的那些技术创新更刺激,也更能造福于社会。”
盖世小结:留给2030年的答卷
从出国到海归,从内燃机到新能源,从企业到高校,彭立新的每一次转型,都踩在了行业变革的节点上。而他当下的“教育改革试验”,或许正是破解汽车行业“缺人才”困境的一把钥匙,当更多高校能跳出传统框架,把“培养工程师”而非“培养技术员”作为目标,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在新能源革命中真正掌握主动权。
与盖世汽车对话的尾声,彭立新回忆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先生,二十多年前专程去底特律的家中邀请他从海外归来的往事:作为海归精英之一,他庆幸当年做出的正确选择,并以能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做出贡献而自豪。
而今,他把最后一段职业生涯押在“育人”上。“时间点只是坐标,真正决定产业走向的,是能不能提前十年把人才准备好。”彭立新说。
栏目介绍
「瞬息万变的汽车产业,如何穿透信息迷雾?盖世汽车集结百位顶级智库专家,直面新能源转型、智驾革命、供应链博弈等产业热战!《专家专论》——以权威视角洞穿趋势,用实战经验解码未来。每一次专访,都是直抵本质的产业真知灼见!」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